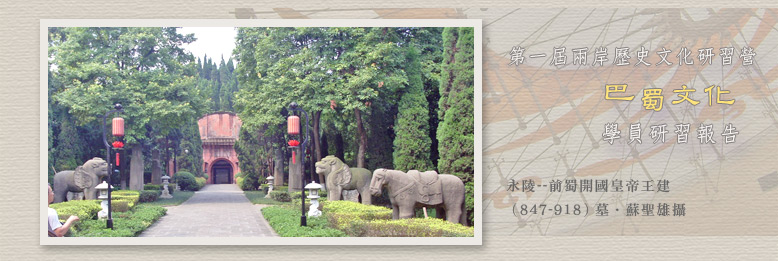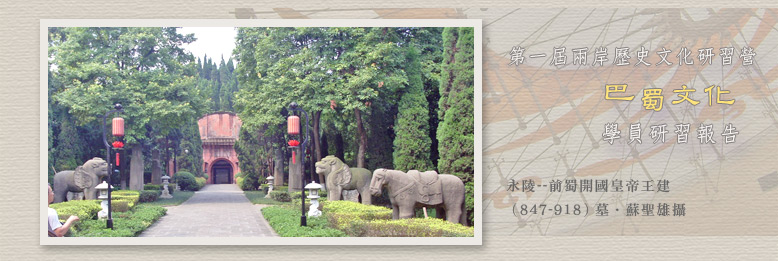本次研習營令我收穫良多,以下依講座、田野與文獻、對未來研究的幫助進行述說。
本次講座請到的講員,學術成就皆甚為可觀,令聽者神遊其中,享受知識饗宴。霍巍院長的講演,不但讓我清楚三星堆本身之歷史,亦讓我知曉開挖的過程。我得以隨著霍院長經歷之重述,獲得清晰的挖掘歷史圖像,並以之與三星堆數千年的歷史結合,將這一切重現腦中。王獻華教授之講座,呼應霍院長講授之三星堆,亦令我重回古巴比倫。尤其王教授深諳楔形文字,令我佩服萬分,能親自見到大師風采,我極感榮幸。黃進興院士之講座,與我近日所思所想完全切合。近日我不斷思索理論對研究之重要性為何,對於套用或創造理論是否必要,甚為困擾。黃院士以親身經歷解答了我的難題──理論不是研究目的,研究對象才是;理論不需要過度閱讀或運用,參考與研究相關者即可。陸揚教授風度翩翩,其講座以墓葬為例,揭示廣泛運用史料之可能。林富士副所長、蔡進先生的講座,則讓我神遊於道教與中醫體系的世界。李孝悌教授之講座,除了讓我看到田野與文獻結合之方法與重要,老師之熱情更令我印象深刻,我以此體認對研究抱持持續熱情之必要。里贊教授之講座對我影響甚大,其揭示運用地方檔案對處理大問題之重要。王東杰教授的研究呈現四川會館的複雜性,惟其未進行田野調查,讓我獲得未進行田野的對比──田野調查,可補僅依文獻進行研究之缺陷,並以此開拓視野。景蜀慧、劉復生教授之講座,則將我帶入杜甫與川中經學家的世界,補充我對這方面的知識。綜而言之,本次研習營之講座,涵蓋層面廣,講員講述深入,令我深受啟發。
以田野與文獻來說,本研習營以成都及其周圍為田野進行考察。三星堆、王建墓、金沙遺址、三聖鄉、都江堰、青城山、洛帶、武侯祠、杜甫草堂、峨嵋山及成都少城等各個地點,皆令我深切體認成都歷史文化之豐碩及複雜。主辦單位發放的文獻,與各講座結合,更加呈現此地之難以掌握。我們學員在好幾次的討論,皆多少觸及這些問題。如討論三星堆之時,對於中原之影響有熱烈的探討。在這些討論中,令我印象深刻者非細節,而是於此認識巴蜀文化絕非一套理論、說法所能概括,其歷史極其複雜,值得吾人深入地方予以探究。
我未來的研究方向延續碩士階段,持續關注蔣介石之相關課題。本次研習營對我未來研究之幫助,可說以蔣中正為核心,由外至內皆對我有所啟發。以最外層言之,呈上所述,本次考察讓吾人深入認識成都及其周邊歷史文化之複雜,若推而及於整個四川,其複雜性更非成都可比;再及於整個西南,甚至中國,其變異絕非任何人所能釐清。蔣介石面對如此龐大、複雜的國家,其如何認知?如何推行其政策?其是否知曉因地制宜之道,抑或其重視單一化,在勢所能及之地強行其意志(如新生活運動、二五減租)?當中中央與地方錯綜複雜之關係,中央權力推而及於地方之實際及影響,都是本次研習營令我深感重要之處。再及於內,過去我看到蔣介石喜歡「車遊」之相關紀載,總覺難以理解,認為坐著車子到處繞有何「遊」可言?進行少量車遊倒還好,若達到喜好的層次,多次車遊,總令我無法想像。本次研習營我們「車遊」三聖鄉,帶著欣賞、崇敬甚至問題在車上思索,令我多少體會蔣車遊之心情:蔣雖常在車遊時與宋美齡、蔣經國及其他高官談事情,但我感到蔣車遊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處理俗務,而是沉澱沉重的心情,藉著景物的變化,名山勝水的靈秀,紓解其壓力。畢竟其身為國家最高領導人,能與他推誠至腹者極少;其喜好於國難當頭、政權危殆之時出訪山水或回故鄉奉化,當與此層關係密切。研習營考察峨嵋山,亦令我對此有深切聯想。我們可以看到蔣介石出訪各地,總會到附近景點「遊觀」,除了藉此與當地政要交流之外,我感到蔣心靈層次的需要,應更為主要。要之,過去我們研究與蔣介石相關的政治史,多注重派系鬥爭,理性判斷,而對於蔣心靈的敘述較為缺乏。我們若要還原有血有肉的蔣介石,將歷史研究做得更具深度,隨著蔣日記的開放,這個層面與過去的取向結合,或許是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本次研習營與國內外各領域學生、老師交流互動頻繁,對我研究產生相當刺激。非常感謝主辦單位及相關工作人員的辛勞,也謝謝同行者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