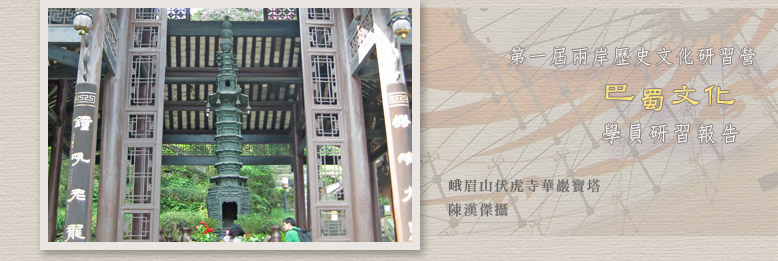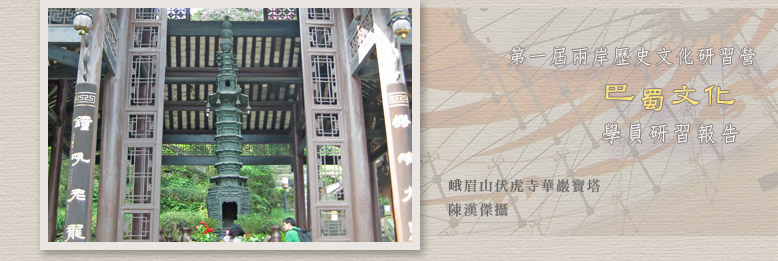成都錦江東岸的四川大學望江校區,因緊臨望江樓公園而得名,這裡曾是錢穆、吳宓等先生品茗駐足之處。有幸能到歷史悠久的川大,參加「第一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巴蜀文化」,不僅是我個人首度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也是首次大量且密集地接觸大陸學者與學生,令人倍感興奮。
從行程的安排,包括學者演講、實地參訪和小組討論,可以看到主辦單位的用心,要使學員兼具思想激盪和實地考察的經驗。所以一連串地上山(青城山、峨眉山)、下海(都江堰)、進城(洛帶、少城區)、出城(自行考察)、出土(三星堆、金沙)、入土(王建墓、武侯祠),就是為了幫助我們瞭解實地情況,進而反觀文獻。在文獻與實景的對照之下,更能凸顯出時間與空間的立體感、交錯感,甚至是斷裂感。讓人深刻地體會到「歷史」並非單純的過去;而所謂的古蹟或遺址也不只是簡單的留存物,而是不斷歷經生滅與再創造的過程。特別是考察途中,當我們陷入所見並非「真跡」或「所剩無幾」的失望時,其實忘了歷史的另一個層面:「現代史」與「歷史的重現(建)」。
「新中國」之所以為新,不僅是政治上新的建制,在改革開放之後更試圖喚回曾經切斷、拋棄或遺忘的歷史,借由找回自己的「舊」以凸顯自己的新。這點,不僅發生於現在,同樣也可見於古代中國。杜甫草堂屢屢重建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宗教上,對於祖庭或大德遺跡的不斷重塑,也是借古開新的例子。因此在現有的遺跡上,我們看到的不必然是真正的歷史遺物,卻是一種延續歷史記憶,或保存歷史的方式。峨眉山之所以值得親臨,恐怕不在於那尊高聳入雲的文殊菩薩像,而是自唐以來賦予它普賢道場的神聖地位,以及日後諸多名僧聖人於此修行的事蹟,所積累下來關於峨眉山的記憶與印象。
因此歷史遺跡之所以有趣,在於它不是只反映一個「時間點」或單純的一樁歷史事件而已,而是過去與現在的綜合體,更精確地說,它呈現了現代人如何保留或運用歷史的努力及成果。這並非否定其歷史價值,反而是具有多重的意義,這包括過去、現在,甚至是未來。以參觀洛帶的會館為例,依據現有會館的情況,我們或許可以研究不同族群,在新居地的發展情勢和特性。這固然必須考索文獻,但也可以參酌會館建築的布局、規模、新舊和精粗,做為思考的起點。進一步,還可探問這些移民族群(或移民後代)的近況,以及他們與會館之間,還有甚麼樣的聯繫或情感?
最後,以一個有趣的例子作為結語。自由行當天,我搭公交前往昭覺寺,參訪初建於唐,曾為宋代臨濟宗高僧圜悟克勤兩度駐錫的叢林道場。昭覺寺曾因局勢動盪而被劃歸隔壁的動物園,後來四人幫倒台,由清定法師進行重建。但不知為何,從動物園獨立出來的昭覺寺,未將圜悟克勤的墓畫入寺區,反而留在動物園內,使得原本想要瞻仰法師的旅人撲了空。不過,這何嘗不是多層歷史積累的結果?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保留歷史(不論是知識或實物)的過程,勢必和現代處境互動,甚至是搏鬥、拉鋸。獲得保留的或歷經重建的歷史遺跡,在也不是過去的「本來面目」,但卻富有更多面向,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