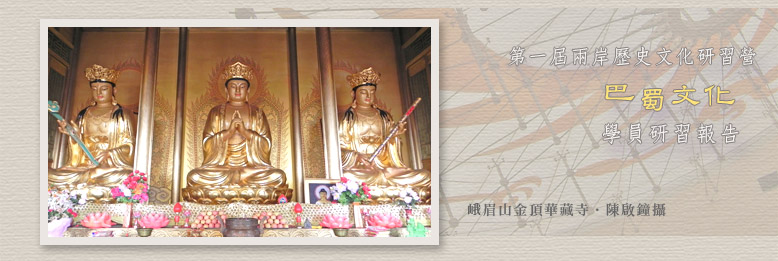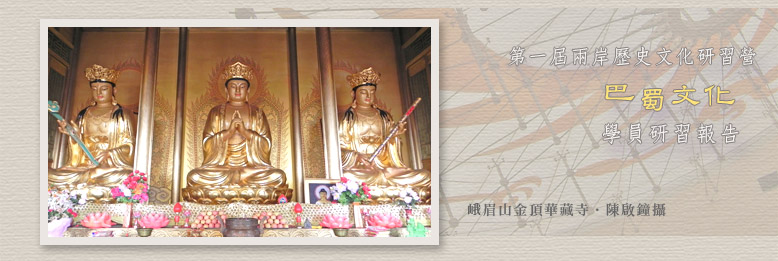遊中有觀:2011 年第一屆「巴蜀文化」研習營心得報告
一、緣起
筆者就讀博士班期間,對區域社會外來人口的歷史現象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長期關注於外來人口與地方社會間的互動關係,最終並以「清代閩北的客民與地方社會」為題,完成了博士論文的撰寫。在此過程中,陸續接觸了研究清代各地方移民的文章與書籍,而清代的四川,正是移民現象最突出和顯著的地區,因此,興起了筆者想要到四川一窺究竟的念頭。
在因緣際會下,筆者得知今年有由中研院史語所、蔣經國基金會、四川大學和宋慶齡基金會等單位所舉辦的「第一屆歷史文化研習營」,希望藉著走進歷史現場,經由田野考察和文獻研讀,對四川的歷史文化有切身和更深刻的體認。心喜之餘,立刻備妥資料報名,也有幸獲得入選,不僅一圓筆者之願,同時還能展開一次具有深度和意義的四川歷史文化考察。
二、演講主題與若干問題省思
為了因應四川特有的歷史文化傳承,此次研習營演講主題和閱讀文獻及於詩詞、宗教、中醫及地方政府檔案等各方面,可說相當地廣泛和全面,在時間和空間上均有所顧及,對於巴蜀文化的理解,具有深入淺出之效。限於篇幅,筆者僅就當中幾個議題進行個人若干思考的論述。
其一,醫官和庶民眼中的祝由。祝由一詞的來源,大部分人認為是出自《黃帝內經》的〈素問•移精變氣篇〉,在元代,成為程試大醫合設科目之一,進入了官方的醫療系統。然而,由於祝由的醫療方法含有高度的宗教與法術性質,到了明代中期後,受到傳統儒醫的質疑,並紛紛要求去除其有違正統醫學理論、系統的部分。事實上,明中期以後的儒醫為了建構明清醫學知識體系,使其更加理性和符合正統觀,才會對含有巫術成份的醫術進行激烈的批判,這並不僅限於祝由,尚出現在其他與其相類似的醫療方法中(太素脈即是其中之一)。由此可知,傳統士大夫的這種批判,應當放在當時的政治、社會氛圍等層次作更全面的觀察,才能得出更為完整的歷史圖像。
再者,祝由歷經儒醫的去巫化言論以後,是否就此消失或有所改變?這可從兩個層面去思考,亦即代表官方思想的醫官系統和代表庶民思想的巫術系統。明代政府雖然從建國之初就設有如惠民藥局、醫官等醫療機構,但實際上,這些醫療機構在地方上並沒有發揮多大的作用,不是被忽視就是被廢棄。明中期以後儒醫的批判,雖然使祝由失去了在官方醫療體系中的地位,但卻沒有影響其在民間醫術中的地位。筆者認為,祝由不僅仍是民間宗教信仰中使用巫術治病的方法之一,甚至所謂的降神治病過程:乩童打坐等待神明附身-施行符咒-治瘉病者,也和祝由的治療程序三階段:祝由者先移精變氣-開始祝由-病者移精變氣,有極高的類似性。由此看來,即使祝由之術被排除在官醫系統外,但仍然活躍於民間,特別是於宗教活動有關的醫療行為中。
其二,地方檔案中案件審斷的依法與否。里贊教授基於四川南部縣檔案的研究,來探討清代州縣訴訟中的審斷問題,並進一步檢視滋賀秀三和黃宗智的爭論何者較接近地方基層社會的審判事實。他認為,根據南部縣檔案所反映出來的情況,大部分案件均未嚴格依《大清律例》裁斷,州縣在審斷糾紛時並未以《大清律例》作為首要考慮,而是常囿於地方習俗和人倫親情,考慮更多的是律例之外的因素。在審斷過程中,州縣並不以是否完成整個審斷程序或給出判決結果為道要考慮,而是以如何解決糾紛為審斷的目標。而州縣在審斷中秉持著解決糾紛的目的,將兩造的告訴當作自己實現一方之治的政務進行處理。在這個處理過程中,州縣不會拘泥於制度規則,而是靈活掌握審斷程序,綜合運用情、理律來了結糾紛。因此,他同意滋賀秀三所言州縣審斷是「父母官訴訟」,實質上是一種「教諭式的調解」之論述。
從地方縣級案件的審判來看,里贊教授的意見是符合實情的。不過,如果拉高層級,從整個中國法律制度的角度來看,則可能有若干需要更進一步分析的必要。南部縣檔案的案件,大多屬於戶婚田土等糾紛的範疇,這類案件的刑責多是笞、杖,因此,其最終審判只到州縣官一級,並不需要往上呈報。基於此,州縣官在審判此類案件時,擁有極大的自主權,可依據自我的意識和判斷來定刑。即如里贊教授所言,地方官所在乎的是地方社會秩序的穩定,至於是否符合大清律例並非重點。(案件關係人兩肇是否遵守判決及如何因應,又另當別論)然而,如果地方案件的性質不屬於此類,而是超越笞、杖以上的徒、流、死刑,由於地方州縣官只有最初審判權和對刑責的建議權,之後尚必須往上呈報,此時,上級長官對州縣官案件刑責擬定適當與否的審查,不僅關係著案件審判的進行,同時也關乎州縣官會不會因為擬刑錯誤而受到處分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州縣官是否能不依大清律例而隨意判刑,其實還有更詳細分析的必要。換句話說,討論地方父母官審斷地方案件是否依據大清律例的問題,必須將不同案件的性質加以區分,並非所有的案件,州縣官都可以不顧法律來解決問題的。從另一面而言,滋賀秀三和黃宗智的論點是可以並行不悖的,所謂「州縣審斷是父母官訴訟,實質上是一種教諭式的調解」和「州縣是嚴格按照清律審斷,他們是以法官而非調停者的身份來行事」兩者,實屬於不同的層級,前者適用於笞、杖刑責的案件,而後者則適用於更高級的徒、流、死刑。
其三,四川移民會館與神明認同。會館的功能可從兩方面觀之:情感的依托及現實的作用。後者又可分為對內和對外,筆者試論述於下。在對外方面,主要是會館與商業的關係和地方資源控制及分配問題。四川移民會館(如湖廣移民的禹王廟、關聖宮;江西移民的萬壽宮;貴州移民的黔陽宮;廣東移民的南華宮;陝西移民的三元宮,以及閩粵移民的天后宮)的位置,主要座落於交通要道、街、場、鎮等地方,無論通都大邑,皆立專廟,雖十室鎮集,亦必建祠。可以看出,這些會館廟宇的建立,都與商業有很大的關係。換句話說,會館廟宇對於移民者的作用,與市場的控制有很大的關係。再者,湖廣和閩粵移民分別以關聖和天后作為本身神明認同的對象又顯示出什麼樣的涵意?關聖究竟是屬於湖廣移民的鄉神,抑或是湖廣移民將地方廟宇納為已有?如果是後者,其動機為何?閩粵移民共同以天后為認同對象,是否是因為相較為湖廣、江西移民,人數上的劣勢使他們必須尋找聯合抵抗異籍移民的可能性?
從文獻材料來看,湖廣移民崇祀關聖的舉動,可以做為筆者上面論述極佳的例子。早在湖廣移民來到四川前,當地就有關聖崇拜信仰,其原本位於城外東溪南岸上,且土著居民禱祀者的數量眾多。在康熙、雍正年間,湖廣移民將關聖宮移至城內東南隅,可以想見,該區應是湖廣移民的聚居地,而此舉正是該移民想要藉由對地方主要廟宇的掌握,來獲得地方資源分配的主導權。為了使此舉合理化,湖廣移民利用林愈蕃的〈增修關聖宮記〉來強調關聖與他們的密切關係,同時著重於關聖的忠誠之氣。然而,關聖畢竟擁有全國神的特徵,湖廣移民將其占為己有,引起了有關該神是特定籍貫所有或所有人共有的爭論,此一爭論,筆者推測,背後尚有地方資源究竟是由某些人獨占或全民共享的意思。換句話說,藉由對神靈擁有權的爭論,要求地方資源的開放與共享。
在移民會館廟宇的對內功能方面,會館是公是公非之所,易言之,即是排解同籍移民間糾紛的地方,因此,能掌握會館者即掌握了處理事務的主導權。這種權力,還可以藉由神明的威望和見證而強化,這是因為主導者可以透過神明降駕、扶鸞等方式來顯示決議的不可違犯性。
三、實境考察-從兩位婦人的談話說起
當研習營一行人到達杜甫草堂時,筆者無意間聽見了雜在學員中兩位婦人的對話:「今天來了一團觀光旅遊團。」此時,縈繞在筆者心裡的是:究竟研習營與一般的觀光旅行團有何不同?對於這個問題,隨著筆者進入草堂後而漸漸有了答案:兩者的不同處,即在於研習營遊中有觀。所謂的「觀」,並非是「觀賞」,而是「觀察」之意。易言之,即是藉由對實境的遊覽,更進一步發掘當中的意義與問題。舉些例子來說,當學員參觀三星堆博物館和金沙遺址時,並非單純欣賞其中有哪些文物,而是更深入地去思考博物館所呈現出來的樣貌是否符合原來的實際情況?三星堆、金沙文化出現的歷史背景為何?其與周邊文化的關係又是什麼等問題;都江堰水利工程所流經的灌溉區域選定過程為何?是有權力競爭的因素在內?地方資源的占有情形和過程又是如何;洛帶客家聚落中各移民會館的勢力消長和地方支配的情形為何?移民會館的建築型式、大小和空間表現又有何意義;杜甫草堂中所陳列幾塊有關光緒年間對於陸游、黃庭堅能否配祀問題的討論反應出什麼樣的歷史意義?這種討論是否代表著一個移民社會向土著社會轉變過程中的文化建設和主導權的爭奪?峨眉山由道教聖地一變而佛教化的歷史背景和原因為何?這些問題和意識的形成與深化,正是巴蜀文化研習營有別於一般觀光旅行團不同之處,亦即不僅遊,尚且有觀。同時,也唯有透過實境的考察,才能在深臨其境中更強化對巴蜀文化的認識,和更深入討論巴蜀的歷史。
四、結語
本屆巴蜀文化研習營對筆者而言,不僅使筆者對巴蜀文化有更進一步的瞭解,同時還有視野和觀念的擴展,特別是王璦玲老師於最後綜合討論中所提出的:當人們去一個地方購物時,並不一定要馬上到所需物品的放置區,也許可以放慢腳步,先看看該處的整體情形,說不定會有更多的體會。這種想法對筆者而言,具有莫大的啟發性:學問的研究,除了專精以外,還需要兼顧博廣,多去觀察事外之物,能讓自己的思慮更加周密和廣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