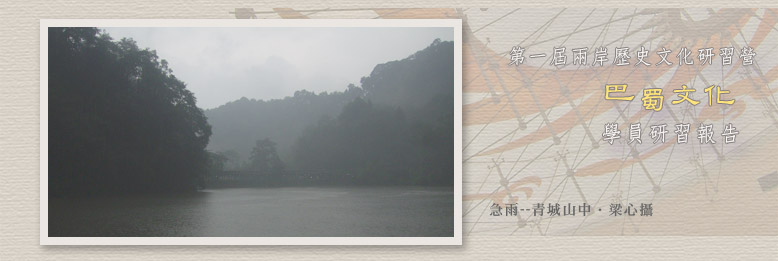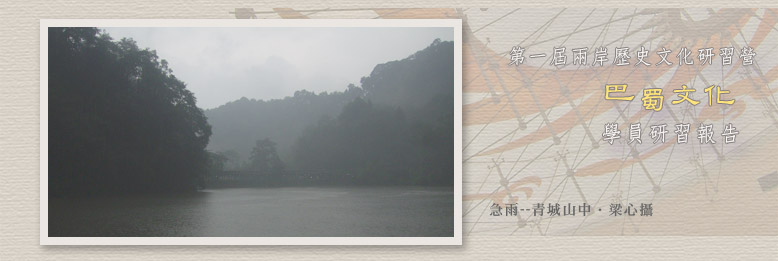2000 年曾經負笈川大,可惜當時年少懵懂,對於所謂巴蜀文化毫無概念——羅老師曾在總結中專門點出「坐井觀天」四個字,大約作為蜀人的我就是坐在井中想像著「天」反而對周遭一切視而不見以至於有了各種奇奇怪怪想法的那一類型觀天者罷。所以,這次研習營能夠讓我以遊子歸人的心態返回來看一個獨特、豐富,甚至在潛移默化中塑造著「我」的「巴蜀文化」,實在是一件非常值得感激和慶幸的事情。
在短短的九天之中,有幸在老師的周密安排下──雖然到了最後一天我才後知後覺的隱約領略到整個課程的深意,領略到了巴蜀文化的各個面向:從尚存爭議指向不明的遠古遺跡,到至今存在於大街小巷中的閒適與逸樂。如老師所提示,同時也尤其引起我慨歎的是,這個地方的歷史一直存在著中斷與變動,卻似乎仍然能讓人看到一些可以被稱為一脈相承的東西。如果說人能弘道,當人都被驅趕,被消滅之後,到底是什麼維持和傳承呢?我不傾向於作出任何決定論的解釋,只是大概能夠看出這樣一個「巴蜀」,它自有其與中原(此所謂中原,大致不可從地理上去理解)「異調」之處,卻也從來不曾封閉自己──所謂異調,大致也是在不斷的跟隨,交流與反省之中形成的吧。
這樣一種文化雖然先在,卻並不虛懸。除了各種各樣的物質之外,更重要的是有各種各樣的人在其中,他們在不斷的觀察,體認和表述著這樣的文化。「巴蜀」不僅僅存在于軍閥,存在于五老七賢,存在於一輩子沒有走出過牛市口的劉咸炘身上,存在於遠走江南尋找經學正統最後卻進入支那內學院學習的蒙文通身上,同時也存在於「湖廣填四川」的移民身上,存在於因為被戲稱為「將合適」(姜何氏)而去打官司的小寡婦身上,存在於因為被說「四川的蛋沒有蛋味」而罵陳衡哲「想做如夫人沒做了」的中學生身上(太過八卦,一笑)。這個地方存在著各式軍閥,卻也肯聽五老七賢的調停。那些希望走出夔門的讀書人想像著一個「中心」,走出去以後卻發現是禮失求諸野,中心早就變了。一輩子沒有出過牛市口的天才學者,可謂閉門造車,卻也有出門合轍的一面,以致至今仍有海外之人前來訪求。而那些來自不同地方的人,開始在這樣一個「十室九空」的地方建設一個「社會」,當然存在著各種「爭奪」,但也每每分享著共同信仰與道德。他們(在現在看來可以被說成是運用法律的手段)維護著自己的名聲,也用(大概是四川人——主要指我自己——特別擅長的尖酸刻薄)維護著這個地方的名聲。在這些人的期望與焦慮中,文「化」的那一面,似乎更易見得;而所謂的「地方」,也在各式各樣的人與各種各樣的表述之中顯得更為明亮飽滿。
再胡思亂想一點,當這些身處於地域中的人(未必時時都想到地域)在忙著期待與失望,在忙著去做那些目標含混,艱苦曲折的事情的時候,甚至忙著想像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他們對這個時代和世界的關係。他們部分人在努力去呼應這樣一個越來越嚮往無差別卻實際上往往反其道而行之的時代,以及這樣一個被後來人描述為越來越小——當然對此也有不少人表示懷疑——的世界;有意回避的那部分人當然更值得注意。時代存乎這些忽明忽暗的事情之中,天下也存乎這些走來走去,或退處一隅的人物之中。坐于井中卻能夠對周遭的一切視而不見大概是最可笑也最有勇氣的行為了,而其探頭出去看到的天,雖然同是天下之人所見之天,卻也可以說是其自有自創的天。「人與人」果然才是最有趣的事情啊。
因此,對我而言,雖然我也非常享受能夠有一次充分融入地方文化(吾鄉地處川北,與成都平原的文化又有不同)的機會,更重要的則是見了各種各樣的「人」——坦白的說,這也是我當初一見到消息就激動萬分的填寫報名表的直接原因。九天中能夠見得各位老師的氣象神采,實在是十分珍貴的記憶;自己也愈發感受到學問那活潑潑的精神。而此間的各種交流與討論,甚至爭執,也讓我看到了大家都分別關心著怎樣的問題,各自的標準、表述甚至基本思考有著多大的差異。這些差異使我——至少在努力以更開放的心態去看待自己所面對的問題,也因此更加感受到了為學的有趣和不易。這對於現階段的我而言,大概是最重要的收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