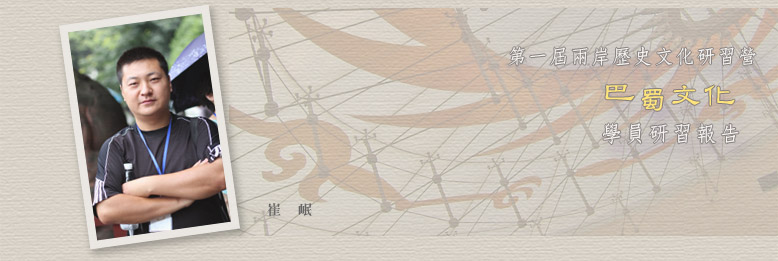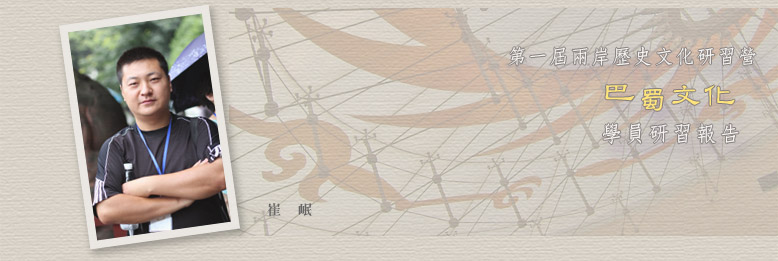對於生在四川,但已二十餘年未曾回過家鄉的筆者而言,此次成都之行本已帶有特別的意味,而研習營的內容更給我留下了頗多收穫與值得珍藏的記憶。
研習期間,上午的報告涉及考古、歷史、宗教、醫學、詩詞,如此密集多樣的學術接觸對我而言尚屬首次。我的專業為中國近代史,有關中國古代史和世界史的知識已屬淺陋,歷史之外的幾個方面更屬業餘,但報告者的講述多能深入淺出,令我不至如聽天書,有些甚至引發我進一步瞭解的興趣,這不能不說已超出了之前的預期。下午的田野考察按主辦方的觀點,旨在「透過實際的田野考察和地方視角,對文獻有深刻而新鮮的體認與解讀」。由於主辦者的用心安排,這方面的效果確屬明顯,除我感受強烈外,還聽到多人談及上午報告下午考察的方式對真切體驗巴蜀文化的好處。
但更令我興奮的還屬晚間的文獻研讀與討論。因報告與田野終係外部資訊的攝入,在研讀文獻的基礎上與營員進行交流則需充分運行大腦,將自身掌握的相關知識以最快速度加以整合,以期提出自認有分量的問題或從容應對他人的質疑。顯然,這一過程對眾人而言皆有壓力,但若積極參與,收穫亦當明顯。或許是組員之間學科差異較大,以及時間緊張的緣故,文獻研讀之後的討論似不如我期待的那樣活躍。
在 8 月 22 日晚的討論中,我對里贊教授的《晚清州縣訴訟中的審斷問題:側重四川南部縣的實踐》一書提出了兩點批評意見,當即引來兩位組員的商榷。不過隨後與他們的辯論以及其他組員的支援讓我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斷。次日里教授的報告結束後,我當面將前晚的意見簡略地再次表達。有意思的是,當日下午在考察洛帶客家聚落時,曾有兩位臺灣營友以不同方式表達了他們的看法。一位好奇地向人打聽我的來歷,表示他被我直言不諱的做法「嚇到了」;另一位則當面向我詢問是否對里教授過於「嚴苛」。這一反應對我啟示不小,因我原以為臺灣學界在學術批評方面應比內地更為開放,當天始知他們或較我們更接近傳統,故對 1949 年以來特別是「文革」後大陸傳統的喪失有了真切的感受。
其實據我瞭解,22 日晚的討論結束後,我的發言便已傳開,次日上午里教授報告前主持人也曾特別提到其專著前晚曾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這似乎顯示出研習營的學術批評氛圍尚顯不足。我以為,研習並非僅只學習,正常的學術批評也應當是其中應有之義。正是由於其他討論都缺乏批評性,我的意見才顯得較為突兀,以致一度成為話題。
最後需要提及的是,此次研習活動對每位學員學術交往圈的擴大起到了顯著的作用。就筆者而言,研習期間不但向李孝悌、陸揚、王獻華、王東杰等學者多有請益,更結識了許多組內組外的營員,他們與我學科不都相同,但與他們的交流同樣給了我學術上的啟發,並建立起了珍貴的友誼。
總之,此次成都之行的收穫超出了我的預期,在此謹向主辦方表達誠摯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