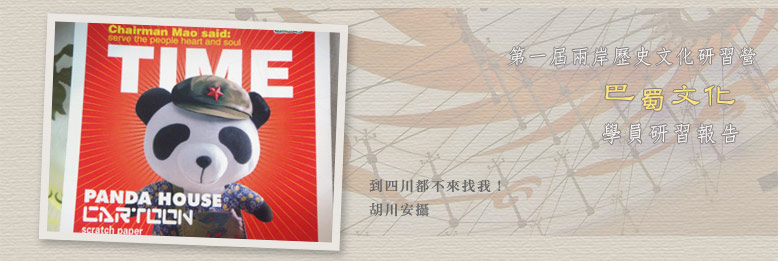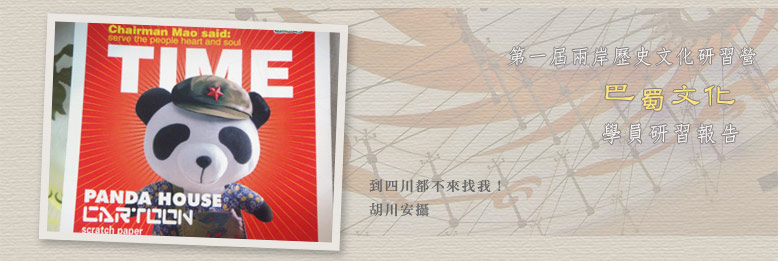在中國,雖然在上個世紀 80 年代以前主要由馬列主義為主導的歷史研究和以國族為核心的歷史敘事方式,但華南學派(指的是由傅衣凌在廈門大學與梁方仲在中山大學所留下的學術傳統和其學生)的努力,仍然在區域研究的領域當中,留下了不少出色的研究。
在西方學界,1980 年代 James L. Watson 所提出的關於晚期中華帝國的「文化標準化」的文章,他認為到了帝國晚期,中國各地之間即使有不同的文化差異,但各地之間在整體上已經形塑了文化上的「標準化」。由此,許多學者展開不同的論述。對於中國地方史的研究者而言,傳統中國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一直是研究者的重要切入點,目前大部分學者都主張應該要給予地區文化更多的主動性,然而,在科大衛的模式中,認為地方社會主動且積極的參與王朝國家的建構,研究中國的地區歷史,就是研究地方如何整合成王朝國家的一部分,這樣的思考方式雖然以下至上來回答這個問題,仍然將地方置於王朝國家的一部分來思考,仍以當代民族國家的思考投射至研究的對象,地方的主體性仍舊無法彰顯。
或許我們應該拋棄中央/地方的二元式思考,「地方」不一定相對於中央,地方歷史的研究者,應該要思考的在於「地方」作為一個歷史的研究對象,它在我們知識形成的過程中如何被認識,「地方」之所以相對於中央,在於一個村落如果作為一個王朝或是國族歷史下的村落,它將在階層性的框架中被認識,它將只是作為國家的邊緣角落被理解,在這樣的架構下,投射到歷史的建構當中,地方史就成為一個一個區域整合進入大一統文化秩序的過程。
但是,如果我們在歷史研究中加入更為寬廣的視角,在不同的視域下與研究方法下,從文化和經濟各種不同的生活面向理解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地方的人群如何理解、認識與選擇自身的生活方式,這樣的歷史將會更加的認識人類生活的軌跡。
這樣的生活軌跡往往不會透過文獻本身透露出來,除了一般的傳統文獻、地方志和檔案外,地方史的研究者還必須透過田野調查和搜集材料的過程,進一步的理解實際的生活空間,透過當代的 GIS 科技,研究者從文化地理學的研究方法,理解人群在地方當中如何活動,將生活的不同面向放進研究資料與方法當中,更加豐富的理解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