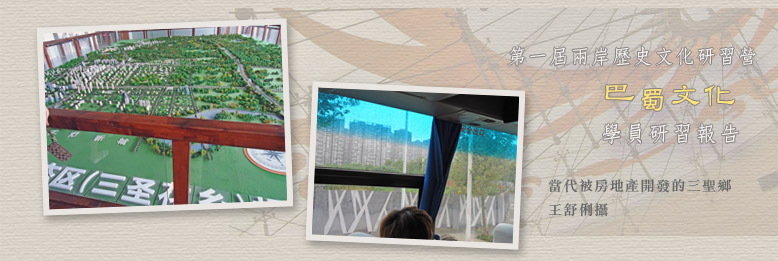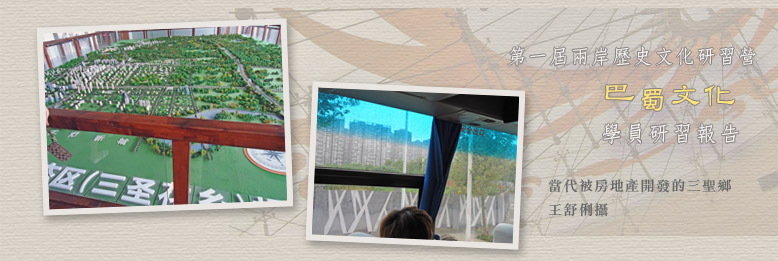成都文化做為展示櫥窗 – 巴蜀研習營歸來
上飛機前往成都的時候,才從倫敦的夏熱暴動之中脫離,此行成都的目的說穿了只是想從煩悶的論文寫作中抽離,到別處散心走走。但是成都到底不是他方,這裡是我論文研究的第二田野地,因此與其說參加研習營倒不如說我懷抱著到此順道做田野的心態參加。可報名時絕對沒料到旅途中會遇到這些感性理性兼具的歷史學家們,結識一群真情真性的朋友,旅途所見所聞更是提高了我研究的視野與對學問的熱情。
之一 治學態度 – 視野與高度
研習營的課程設計巧妙,早晨有兩位老師分別授課,下午實地參訪,晚上回到川大有分組討論與大班綜合討論,於是每天結束回到旅館往往已是深夜。第一天開場的是黃進興老師,我在大學的時候與好友一同跑去文學院旁聽他開給高年級的研討課 -- 儒教,即便他課堂中提到的許多史學家與理論背景我聽得懵懂,但當時總覺得聽他的課本身就是一種享受,特別是這些沒聽過的史學大家與深奧理論在打擊信心之餘總能激起我對知識追求的熱情,因此即便每週得坐校車往返總區與法學院也是甘願。多年以後再聽黃老師講述思想史,聽課後又是一番慚愧,我自恃這幾年的苦讀理應稍為踏入門檻,但與老師那游移中西貫穿百年思想史的境界與治學的態度相比,還是相差太遠。於是一番熱情又被燃起。晚上的討論課更是激烈,大家環繞在黃老師拋給大家的議題,除了討論大陸與台灣史學課程殊異,也分享個人的學思歷程,到底理論是否必要?
由於研習營每天都有田野實習,因此常有機會藉著出外走動與許多老師交流。我和子雅特別喜歡和王璦玲老師相談,因為她的優雅與感性總讓我覺得像紅樓夢走出來的人物。璦玲老師總是叮嚀我們,做學問靠得是熱情,而不能期待賺大錢。沿途中有機會和王獻華老師多番交流,知道王老師的學思背景從哲學、基督教研究、物質理論與人類學,到圖像研究與考古學,讚嘆佩服之餘,我想我們這群作文史研究的人,都有如同黃進興老師所言的那番傻勁,怎麼能夠叫我們不念書?!於是多年以後我也明瞭,其實我聽黃老師的課從來獲得的不是理論不是知識,既非儒家是否為宗教也不是思想史是什麼,而是治學應處的視野、高度,與熱情。
之二 成都文化做為展示櫥窗
1. 地方史與國族史
研習營的前兩三天就是到三星堆與金沙博物館,從博物館展示陳列敘事來看,一方面這兩個館將考古發現的材料與當時同屬青銅時期的安陽殷墟作對比,另一方面,兩個館不同於許多中國大陸的博物館,他們都沒有特別論述整個中華文化的歷史發展,由於三星堆與金沙博物館同樣都隸屬於地方,因此展示內容是從四川當地開展對地方的歷史建構。這裡除了可以思考胡川安同學在分組討論時不斷想要解構中心與邊緣的相對關係,另一方面,也可以思考成都,或者是蜀地,如何在當代去建構一個不同於傳統中國史學放在中原歷史的蜀地史。我記得兩年前到成都的第一場拜會就是霍魏老師給我講授成都地方文化史。當時他的講述方式讓我訝異,因為過去對於中國史的了解比較放在中原,並以朝代更迭來了解,而現代人類學在處理中國大陸社會研究時也只從當代去分析地方與國家的關係,在思索國族與歷史問題時往往忽略地方史的傳統。而這次歷史研習營中,包括三星堆考古發現、西南地區的會館文化、司法判例等等有關地方誌的課程,都加深了我對於地域文化的了解,也意識人類學研究不應該忽略地方誌的傳統。
其次是關於地方史之於國族史建構的關係,這些與我目前論文研究探討當代文化遺產的運作脈合。當整個中國極力地將「過去」做為一種文化資源來開發,成都展現了一個極大的企圖心,將許多文化古蹟、歷史名人的故事、文化典故,做極有力的包裝,對外展現自己。在景區之外,比如都江堰這幾年的李冰的祭典,金沙博物館農曆春節時的金沙文化節,都是以蜀地出發,將景區的內容再度深化做擬真式的呈現,這些企圖讓成都本身在當代中國的區域文化中獨樹一格,其文化景區與博物館的數量與遊客足以和西安、北京等歷史古都媲美,也使得蜀學放在當代中國研究中自成一派。
2. 知識份子與個人性
記得霍老師曾經提到成都之所以不同於中國大陸其他地方,在於這裡有許多文人雅士環伺在掌權者身邊,他們可以有機會對地方文化的發展提供意見。李孝悌老師關於知識份子的論述讓我想到自己論文研究對於當代中國大陸的個人在推動地方文化遺產改造時的所能扮演的角色。有機會與李老師相聊,又是一番醍醐灌頂。向來當代中國研究對於大陸社會的討論,都視中央政府為一個巨大的國家機器,而缺乏個人在其中可以扮演的角色,可是李老師的文章讓我想到,是否過去儒家知識份子為大社會大國家奉獻的情懷還做用在當代社會中的個人對於國族建構的想像呢?李老師也特別提醒,或許不應該忽略共產主義教條下一個好的黨員之於社會應盡的義務。其間我們還有許多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討論,於是乎本來我的論文書寫正卡在如何從個人性、地域性與地方文化特性的角度切入來賦予我的文章更高理論深度,透過旅途見聞與跨學科的交流,一時之間靈思泉湧。
3. 當代文化的打造與歷史呈現
站在人類學家的角度而言,許多觀光化的景點,對我而言有些過度的包裝,只是做為當代觀光客的凝視 (tourist gaze)。比如我一向覺得寬窄巷子是 somewhere that local people seek for exoticism and foreigners seek for authenticity. 這些歷史景區的打造絕對不是復原過去的景點,因為他在當代之中,讓我們對於過去有些想像。可是其實我也不斷在思考,所謂「真實性 (authenticity)」到底是甚麼?因為歷史本來就是不斷在被建構之中。
旅途中看黃老師與師母悠遊杜甫草堂與武侯祠詩情畫意,看到王璦玲老師興之所致高聲黃梅,看李孝悌老師與陸揚老師在峨嵋山道觀的沉迷,看同學們興致盎然,大口吃肉、大口喝酒、高談闊論,如果對於這些研究歷史的歷史學家們,置身觀光化的景點,還能與歷史對話,能夠展現他們對於學術的熱情對於生活的感性,這樣想來,當代成都企圖利用文化歷史來展示自己,也是一種成功吧?
研習營是在王璦玲老師與李孝悌老師優雅高揚的黃梅調中結束,他們那溫柔感性的聲與影,時而激盪高昂時而悠緩低喃,貫穿了我對於此行成都的浪漫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