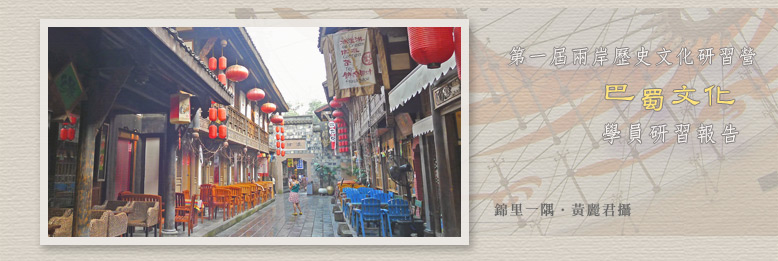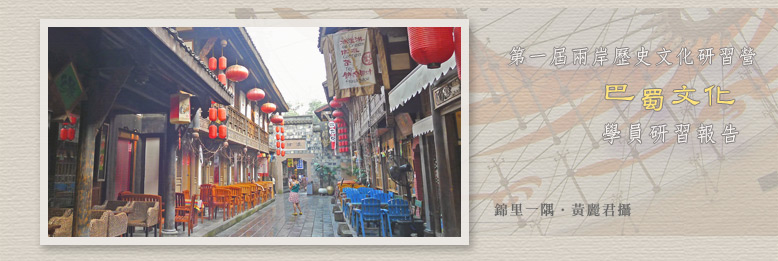此次我被選中參加首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並全程參加活動,感到十分榮幸。並且其規格之高、內容與過程之新穎,未到成都前著實沒有想到。因為以往也參加過國內舉辦的講習班,但並沒有學員之間的公開交流討論,也沒有田野考察這一項。交流討論可以識人交友,田野考察可以察地觀風。至於老師們的講座,同樣很精彩,使我領略了從未領略過的臺灣學者的學術風采。以前我以一個內地學生的孤陋寡聞,總願意把港臺海外的學者看成鐵板一塊,這次參加活動我也認識到確實並不如此,有腳踏實地的,也有「在外太空飛來飛去的」(黃進興先生語),不一而足。
考察的觀感,巴山蜀水確實與我所常見到的北方山水不同,應該說巴蜀的山水更有質感,給人無窮無盡的感覺,一層又一層,我以前雖然知道青城天下幽這話,但想像不出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而真正站在它的山門之外,真正感受到了這種難以言表的幽寂。與此相關的,就是此山此水陶練出的蜀中之學的魅力。通過劉復生、羅志田老師的總結與課後及返校後閱讀蒙文通、劉咸炘的論著,特別是點讀劉氏的《蜀學論》,使我對蜀學的認識更加親切,從宋代的龍昌期到近代的劉、蒙二氏,蜀中學人總給人以恢詭譎怪的感覺,其學則以規模宏大見稱。
再回來說參加討論的感受,這是生平頭一次與很多臺灣學員坐在一起交流,臺灣學員對材料的解讀往往能夠通過史料找到或抽出某些學術概念,進而將它們組織成一個比較宏觀的問題,比如地域文化特色與地域認同,以及性別意識等等,顯示了他們深受西方社會科學的影響,這一點大陸學員的表現似乎並不突出,至少大家在這方面的表現並不整齊。這是我參加討論後獲得的一點很深的印象。研習營中來自臺灣的導師的講座同樣加深了這種感受。我想這是否是臺灣史學界的一種風氣。我想這往往足以使我眼前一亮,迅速產生具體問題,進而再從史料中去研尋、獲取答案。重視社會科學的研讀,以社會科學方法治史,不單是我的感受,也是與臺灣學員交流中親自感知的。比如在去往峨眉山的路上,史語所的廖宜方兄捧讀施特勞斯的《憂鬱的熱帶》,並戲稱這是「旅遊文學」;朱開宇兄有一次曾開導我說要多讀些西方社會科學的書。不過,就我所參加討論的情況來看,我比較懷疑這種方式是否能真正對文本有所深入細緻的解讀?我看到有的組員以文本中的一句話,甚或一個詞,就生發出比較大的問題,反而忽視了文本體裁與行文自身脈絡所體現的、作者本身關注的問題。
記得最後一次集體討論時,老師們紛紛說這項活動很成功,以後還會再舉辦。因此我想就此次參加研習的感受提幾點建議。首先是,能否考慮少而精當地安排就近外出考察,以把時間更好地用於在地考察;再者希望能夠給各位老師以充分的時間鋪展他們精彩的學術見解;關於分組討論,我覺得這個項目比其他同類講習班的優勝處很大程度上在此。我想正如 Nicole 所說的,材料似乎可以事先發給學員,或把目錄發給大家,先行研讀;先行研讀的好處就是我們在未去之前可以閱讀或收集相關的文獻,我想這樣無論聽課還是討論的收效都會更好。
在成都,我結識了不少談得來的同學、友人,並且我還首次見到了有宗教信仰的友人,大陸、臺灣都有,他們帶給我的影響是不小的。最後我想再次感謝組織者的悉心安排和川大老師同學們的細心照料!希望與師友們在以後的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中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