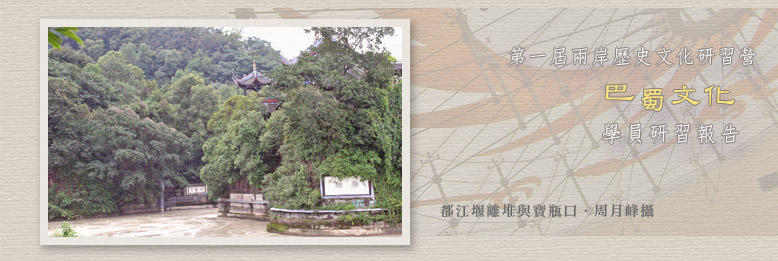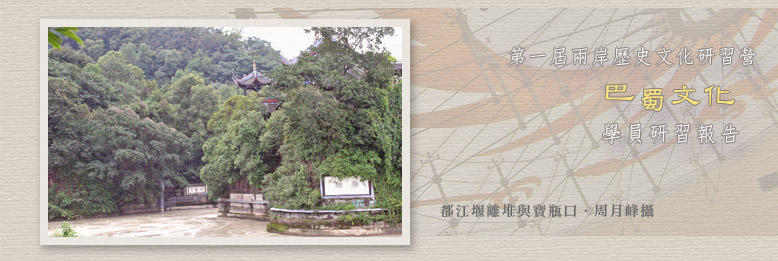史無定法:多元與開放的巴蜀文化研習營
在參加巴蜀文化研習營之前,我未參加過其他的研習營。就平常接觸或耳聞的一些情況而言,感覺一般立意多為「方法訓練營」:在較短時間內,儘量示範一套找材料、讀材料、用材料、思考問題的方式。也許通過這樣的研習營,學員確實比較容易上手,可以學到一套在某些領域較為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參加巴蜀文化研習營之前,我亦是如此想像。而參加後的結果,卻是出乎意料,且驚喜頗多。
最明顯的特色,即這不是一個以一套方法訓練學員的研習營。相反,主辦者刻意提供不一樣的材料、不一樣的方法和不一樣的表述。正如羅志田老師在總結中所說:「希望儘量容納不同的領域、不同的研究取向,以及不同的表述取向。」如果說有些研習營是在一種「家學」示範中讓學員進入一種「門戶」,那這個研習營恰恰相反,基本上是打破我們眼界上的門戶,儘量讓我們的視野開放。
這一點,在各老師的講演中有充分體現。
霍巍老師基本展示的是一個考古學者看三星堆實物的視角與方法,從實物與實物的聯繫看三星堆與中原文化、長江下游文化的聯繫與異同;王獻華老師講古巴比倫,材料雖同樣是有文字之前的考古材料,而其所使用的幾乎全是讀文字材料的視角——將文字本身當作歷史遺留下來的材料,然後從文字到符號到圖像,反向解讀考古材料,來思考古巴比倫的王權與社會,並嘗試給我們展示一種解讀傳說時代非文字材料的方法。而陸揚老師在使用五代墓葬材料時,更多的是在體會一種時代風氣的轉向,然後借助圖像和文字材料來捕捉改變中的唐末五代政治文化風氣。怎麼使用實物或圖像材料,是近十幾年來史學界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這次研習營將這一問題以「見之於行事」的方式展現給我們,三位老師雖然都使用了考古材料,但取向與方法卻絕不相同。
又如里贊老師在講晚清州縣審斷時,邏輯鮮明,在回到州縣審斷是政務非司法的基本視角中,一步步將審斷過程展現出來,清楚明瞭。而王東杰老師在談論清代方志中四川移民的「鄉神」祭祀與身份認同時,儘量展現方志敘述中原有的文脈,枝葉扶疏。特別是「說法」這一觀念的使用,不只有助於我們對方志撰寫者的理解,對我也有理論與方法的啟示。
林富士老師從「祝由」一事探討道教與醫術問題,李孝悌老師探討明末地方士大夫的心靈、生活世界與地方文化的關係,雖然兩個問題的內容在時空上差別很大,但思路有相似或相通之處,希望返回到歷史上的「當下」,進入當時人的頭腦之中,從他們的視角去體會與觀察他們的世界,以儘量「重現」各自歷史時期的多樣與複雜。
以上一些僅僅是我個人聽講過程中的初步印象,或有誤讀或有偏見。但「可以從無數角度去使用材料和體會歷史」這一點,對我而言,卻是真切與揮之不去的。這種材料、取向、方法、表述的不同,十分明顯,足以讓我體會到「什麼取向都可以做好史學,什麼材料都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過去」。但如果這僅僅只是上課,可能會弱水三千取一瓢飲,對一種自以為理解而性之所近的取向與方法會思考多一點,但研習營的不同之處,是在聽完之後還有討論。
研習營的學員來自大陸、臺灣、美國、日本、新加坡,受不同教育,不同專業,來自不同師承,有著不同的學術訓練。這與之前在同門或同班同學之間的討論很不一樣,同門之間歷年下來,時時討論,有小異,但總體而言,在基本的思維方式上已漸漸趨同。但在研習營中,有些觀點提出來時,自以為不言自明的東西,會被從根本上質疑。對材料、方法、表述的看法更是各不一樣。基本上是對學術的理解和對學術的評價都有很基本的分歧。在這種情況下的討論、爭論一方面讓我重新審視自己以前的一些看法,一方面使我試著站在別人的角度與立場上去體會。在平時的接觸中,學員還有更多討論的時間,比如在聽完陸老師涉及五代墓葬的講座後,我曾分別請教過學藝術史和考古學的同學,發現他們各自看重的與陸老師所看重的絕不相同。這種根本的多元與分歧,是始終伴隨著研習營的。
在巴蜀文化研習營中,不管是演講或討論或考察,也許並不能立刻化成某種方法,體現在我們的具體研究中。但我想,這種開闊的視野與開放的態度,也許會在之後的研究中慢慢發酵,甚至使自己的研究形成一種根本性的轉變。史無定法,這是一個讓我來的成都解放思想,再重新出發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