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元讀物
|
第三部:環境與公共衛生 |
單元十一:公共衛生的興起(鄭雅文)
公共衛生的興起
鄭雅文
台大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一、 前言
在當代社會,公衛議題越來越切身,不時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舉凡傳染病防治、疫苗接種、食品藥物安全、醫療行為、醫病關係、醫療照顧體系、環境污染防治、職業傷病的認定與補償、生育政策、健康行為的介入等等,無不屬公衛領域的議題。
從其他學科領域看來,公衛似乎無所不包,但也因為如此,公衛的疆界與定位時常備受質疑。例如,預防醫學、生物統計學、環境工程學、心理與行為科學、社會福利政策、經濟與法律學等學科,皆與公衛有不少交集。究竟公衛學科與其他學科如何區隔?是研究理論或研究工具的差異?還是研究內容、研究主體,抑或是價值觀點的差異?而為何有些健康問題成為了「公共」問題?有些健康問題卻未成為公共議題?國家以什麼依據介入健康問題?國家採取什麼手段?國家公權力又代表了誰的利益? 透過歷史回顧,將讓我們對於公衛的本質,有更深入的理解。
現代意義的「公共衛生」發韌於十九世紀的歐洲社會。西方國家為了管理社會秩序,同時也為了富國強兵、拓展海外政治經濟勢力,積極地推動各種人口健康治理政策。同時,人權意識的提昇,以及來自於社會內部的政治社會改革壓力,也迫使國家不得不承擔起保護民眾健康的責任。公衛學科的發展過程,除了受到人口健康問題的本質,以及科學、科技知識的影響之外,更與國家角色的擴張、人權意識的啟蒙、疾病因果論述的轉變,以及政治社會運動等因素息息相關。
公衛的發展歷史,可視為是人類社會追求健康與福祉的發展史;這段歷史充斥著各種利益衝突,公衛的介入策略也一直處在各種社會爭議當中。本章以西方國家的公衛發展經驗為主軸,首先回顧人口轉型以及疾病問題轉型之歷程,接著介紹公衛學科的發展緣起與轉變,並指出公衛社會歷史的分析主題。
二、 人口轉型與人口問題
人口組成與人口數的變化,乃是瞭解人口健康問題的重要基礎。人類社會在步入農牧社會以來,人口轉型過程雖不盡相同,但大致可區分為四個階段;以下以西歐與北歐國家的經驗為例(參見圖一)。
圖一:人口轉型:以西歐與北歐國家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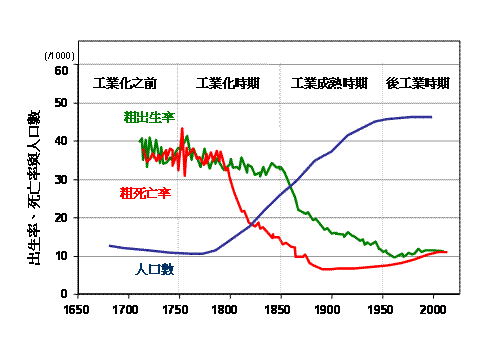
長久以來,人類社會飽受疾病、瘟疫、糧食不足、生活環境惡劣等因素所限制,人口成長緩慢,乃屬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幼年人口較多的人口結構。至十四世紀中葉,黑死病造成歐洲人口遽減,引起極大的社會恐慌。
進入十五世紀後,歐洲社會經歷文藝復興與科學革命,人口數逐漸增加;隨著國際貿易日益蓬勃,歐洲人也開始向海外擴張勢力,例如,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紀征服美洲,荷蘭人在十七世紀(1624年)登佔台灣。在早期,國力大小往往由統治者掌控的人口數來呈現;生命統計(vital statistics)成為重要的人口治理工具。英文statistic一詞由statecraft衍生而來,即指(Porter 1999)。
早在十六世紀,英國便已設置了例行性的人口死亡率統計(The Weekly Bills of Mortality)。到了十七世紀中葉,英國醫生葛盎特(John Graunt)運用這些統計資料,發表了「死亡率的自然與政治觀察」(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報告書,其中詳細描繪英國人口的變化趨勢,包括死亡率、生育率、初生嬰兒死亡率、嬰兒性別比、死亡率季節變化等等,他也發展出「生命表」(life table)分析方法,並作跨區域比較。這些分析方法成為人口學的基礎。至今人口統計仍是公衛領域的必備工具,也是政府人口健康政策的重要依據(Beaglehole and Bonita 1997)。
歐洲國家自十八世紀中期展開快速的工業化革命。機械取代了人力與獸力,讓糧食生產量大增,此時人口死亡率急遽下降。以英格蘭與威爾斯(England and Wales)為例,人口死亡率在1820年之前即已呈現快速下降的趨勢(McKeown 1988)。
在快速工業化時期,人口數亦呈直線上升;農村勞動人口大量地湧入新興的工業化都市。很快地,都市環境由於工業污染與人口暴增而變得污穢不堪;貧窮、飢餓、疾病,以及人們怨恨不滿的情緒,也在都市貧民窟中蔓延開來。統治者原先對於勞動力不足的擔憂,很快地被勞動階層生育率過高的焦慮所取代。
1798年,英國學者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發表了著名的《人口論》(Essay on Population)。他預測,人口數將以倍數成長,而糧食生產量勢必難以追上人口成長的速度。為了避免糧食不足導致的飢荒問題,馬爾薩斯主張,必須透過積極的生育控制來降低人口數;然而,他又悲觀地認為,窮人缺乏道德約束力,只會越生越多,因此,與其讓眾多窮人浪費掉有限的糧食資源,不如透過飢荒與疾病等機制,淘汰掉部份人口。他主張,救助窮人將對社會整體的發展與人類文明的進化產生負面影響。對於奉行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經濟政策的新興資本家而言,救助窮人或是保護勞工的措施不但增加生產成本,也會造成貧窮人口暴增。《人口論》提供了疾病問題不應干預的論述基礎。
1859年,達爾文(Charles Darwin)發表《物種的起源》(The Origins of Species),提出以天擇為機制的演化論。但生物學上的演化論,轉化為「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對那些支持自由競爭、優勝劣敗法則的人士而言,濟弱扶貧的社會政策,反而被視為是違反自然天擇、阻礙人種進化的不當作為(Hamlin 2002)。
十九世紀歐洲社會的人口暴增問題,藉著大規模的人口外移而得以抒解;但大量接收歐洲移民的美洲與澳洲,也在19世紀末期面臨人口過度成長,以及勞動階層普遍貧窮化的問題(Fee 1997; Porter 1999)。
國家到底應該如何處理工業化過程中伴隨的人口激增問題?應如何控制生育率?是否救助窮人會造成貧窮人口的增加,反而造成貧窮問題的擴大?這些爭議,成為西方工業化時期人口政策的核心。
大多數國家在進入工業化社會一段時期之後,出生率即開始呈現顯著的下降趨勢,進入人口轉型的第三個時期。以英格蘭與威爾斯為例, 出生率大約在1870年左右開始下降(McKeown 1988)。出生率下降的原因是多重的,包括工業社會的家庭支持體系改變、家庭所需要的勞動人口數降低、嬰幼兒存活率提升、養育子女的成本上升、婦女社會經濟地位提昇,等等。簡言之,人們為了提昇自身生活品質而設法控制子女數。生育率下降也與人們越來越能掌握生育技術有關。
自1950年之後,西方先進國家步入以服務業為主的後工業時期,人口死亡率與出生率趨於穩定,形成低成長率的安定人口結構。但生育率過低、甚至低於人口替代率,成為另一個人口政策議題。在目前,除了擁有龐大移民人口的美國之外,大多數先進國家都面臨生育率過低與人口老化的問題。
放眼其他國家,如同西方國家的經驗,工業化過程也伴隨著死亡率與生育率的變化,以及人口數的遽增;但相較於西方國家大約經歷兩百年時間,新興開發國家的人口轉型過程更為快速而顯著。
以台灣為例,自1905年左右開始有較正式的人口統計資料以來,死亡率即呈現快速下降的趨勢。出生率則至戰後1951年達到高峰,之後呈現急遽下降趨勢,至今台灣婦女的生育率仍持續下降,已是全世界排名數一數二的國家了。在人口數方面,日本政府在1905年進行第一次人口調查,當時人口總數312萬人(3,123,302人;含日籍人士59,612人),至2009年達2,312萬人。台灣人口成長最快速的時期在1950年至1980年間。
圖二、台灣的人口轉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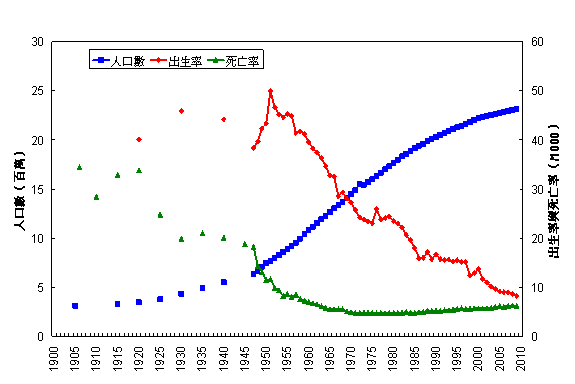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內政部統計處、Mirzaee (1979)。
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推估,世界總人口數在1750年左右約有8億,至1950年時增加至25億左右;但1950年之後全球人口暴增,至2000年時全球人口已逾60億。推估至2050年,世界人口可能高達90億,而絕大多數人口將來自中國、印度、南亞及非洲等主要來自新興開發國家。
圖三、世界人口數的變化
(單位:10億,billions, 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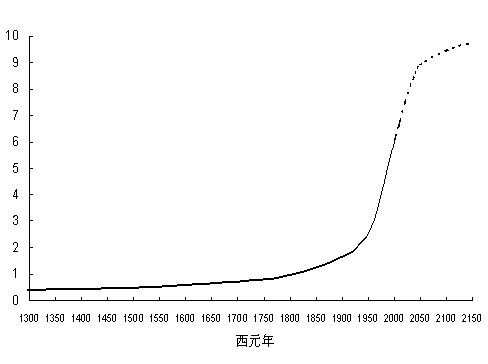
資料來源: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ited Nation
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sixbillion/sixbillion.htm ; 搜尋日期:11/2/2010)
三、 疾病的轉型與預防策略的轉變
人類的歷史,亦是一部疾病的歷史。自古以來,人們便積極尋求各種驅避疾病、延長壽命的方法,每個社會也各自發展出保健強身、預防疾病的策略。在西方,舊約聖經的利未記是最早的衛生典籍之一,其中記載著痲瘋、癲癇等疾病,也已有不少保健策略,包括食物的選擇、身體的潔靜、染病者的隔離、住宅的消毒等等。
在古希臘時期,被奉為西方醫學之父西波克拉底(Hippocrates)提出「體液論」(Theory of four humors),認為自然界是由空氣、火、土、水等四個元素所組成,而人體也是由這四個元素所相對應的體液所組成,即痰、血、黃膽汁、黑膽汁。古希臘人認為,疾病的發生,與體液的失衡有關;他們也觀察到地理風土、氣候、季節等環境因素對人的體質、性格,乃至於疾病的影響。古希臘人注重環境與體液的平衡,採取的保健策略包括住所的選擇、空氣與水的流通、飲食均衡、身體清潔、體格鍛鍊、生活紀律等等(Rosen 1993 (1958))。
羅馬人接收了古希臘人的保健觀念,尤其是水道工程的建立,乃是羅馬文明的重要特色。早在西元前312年左右,羅馬人便已建造了供水道,用於飲水、噴泉、澡堂等設施。此外,羅馬人也已建立了污水下水道,部分古羅馬時期的下水道仍存在,成為現今羅馬下水道系統的一部份(Rosen 1993 (1958))。
「體質論」與「環境論」長期主導著歐洲人對於疾病因果觀念。但在中古時期,歐洲社會籠罩在濃厚的宗教氛圍中,教會要求人們摒棄世俗享受,致力於精神層面的提升,古希臘人所注重的環境清潔、健美體格與飲食保健之道,在此時期反被認為是耽溺於物質生活的行為。人們普遍相信疾病的發生是上帝的旨意,除了懺悔與祈福之外,似乎少有積極的介入策略(Rosen 1993 (1958))。
直到14世紀中葉黑死病一再爆發,短短幾年間歐洲人口大量死亡,不僅社會秩序崩潰,也衝擊既有的宗教與政治權力結構,統治者開始採取積極的防治策略。在疫病蔓延的時期,染病者往往被拘禁在自己家中,受感染或疑似有感染的船隻及旅客,也被禁止入港。至1377年,義大利地區的港口規定,來自疫區的旅客必須留在港外指定地點40天,確定沒有發病才准入港,成為「隔離檢疫」(quarantine)政策的濫觴(Rosen 1993 (1958))。
歐洲社會在15世紀經歷文藝復興,知識逐漸普及;自16世紀以來,以物理學為主的實證科學快速發展,也帶動了解剖學、生理學與微生物學的發展。早在16世紀,義大利醫師Fracastoro便提出「微生物致病論」的說法,他認為疾病是藉由所謂「疾病的種子」(spores of disease),透過直接接觸或間接接觸而傳播。在17世紀,荷蘭科學家van Leeuwenhoek從自製的顯微鏡中觀察到微生物。在19世紀初期,義大利昆蟲學家Bassi發現了寄生在絲蠶體內的微小生物,德國解剖學與病理學學者亨利(Friedrich GJ Henle)亦提出「微生物致病論」的論點。然而,在霍亂不斷爆發的19世紀中葉,衛生物究竟如何致病,卻尚未得到證實。
18世紀,歐洲社會進入快速工業化時期,由於都市人口暴增,造成環境衛生日益惡化,加上貧窮與戰亂,群聚性的傳染病如霍亂、傷寒等快速蔓延。在19世紀中葉,歐洲大城市一再爆發死傷慘重的霍亂疫情。當時國勢如日中天的英國,在1831、1848、1853、1865年連續爆發霍亂大流行,每次都有成千上萬的都市居民死亡,引起人們極度恐慌。在病因及感染途徑不明的狀況下,都市窮人與污穢狀況,成為眾矢之的。但基於「感染論」(contagious theory)而採取的傳統隔離措施,並無法防止霍亂的蔓延(Tesh 1988)。
此時人們相信污水及排泄物伴隨的臭氣,可能是致病主因,歐洲社會開始推動大規模的都市環境衛生改革。「瘴癘論」(miasma theory)逐漸取代「感染論」,而都市裡窮人聚集的污穢貧民窟被視為是疾病的禍源,而都市環境的整頓也成為迫切的議題。政府官員查德威克(Chadwick)奉派至貧民窟進行調查,並在1842年出版了『勞動人口衛生狀況報告』(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ring Population)。此報告書指出,污穢骯髒的環境,包括污水、瘴氣臭氣、排泄物、垃圾等,是造成疾病蔓延的主因,查德威克因此主張應該建立下水道來排除污水瘴氣、建立上水道確保飲水衛生、建立廢棄物處理機制、制訂喪葬規範等等。1848年英國再次受到世界性霍亂大流行波及而死傷慘重,也促使「公共衛生法」(The Public Health Act)的通過,成為世界第一個以中央政府的公權力介入公衛事務的法源。「公共衛生法」以查德威克的報告書為依據,並透過維多利亞時期威權的中央政府強力推動,在中央設立「國家衛生委員會」,在死亡率超過23‰的地方強制設立「衛生委員會」,以推動衛生改革(sanitary reform)。此法促成了19世紀中後期歐美國家大規模的都市衛生改革,查德威克也被視為是現代公共衛生之父。
英國訂定「公共衛生法」之時,歐洲正處在革命浪潮最高漲的時期。1848年法國爆發了影響深遠的政治革命,試圖建立全民普選以及確保全民工作權、生存權的民主共和體制;此年也是馬克斯(Karl Marx)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以德文出版「共產主義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的一年。在社會暴動與政治革命的威脅之下,溫和中庸、工程技術取向的都市環境衛生改革,很快被英國皇室採納,也受到工業資本家歡迎。英國皇室與其它歐陸皇室不同的一點是,英國的皇室貴族階級與新興的資產階級密切結合,也不斷吸納社會菁英與工業資本家成為貴族階級,而歐陸的封建貴族則往往與新興的資產階級對立。對英國資本階級統治者而言,改善窮人的生活條件,不僅可防止傳染病,又可疏瀉民怨,防止激進的社會革命。此外,從功利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觀點來看,國家投資公共衛生也可確保勞動力的健康,降低社會救濟支出,乃是有助於國家產業發展的有效投資。
到了1880年代左右,Henle的學生科霍(Robert Koch)成功分離出炭疽菌、肺結核桿菌與霍亂弧菌,法國的巴斯德(Louis Pasteur)對發酵過程的研究也受到證實,「細菌致病論」成為生物醫學的一大突破,也成為二十世紀以來最主流的疾病因果論述(Rosen, 1958)。
十九世紀後期,西方國家進入了殖民帝國時期,國家開始積極擴展人口治理權力,在富國強兵的考量下,之前強調個人自由、自由放任的社會經濟政策,也轉以國家利益為重,主張個人利益和自由在必要時需要受到限制。
十九世紀後期也是「細菌論」確立,微生物學成為疾病防治主軸的時期,公衛的內容從之前的都市環境改革、社會改革,轉入生物醫學領域。而海外帝國主義擴張與國際競爭的經驗,更讓資本主義國家體認到疾病防治與熱帶醫學的重要性。
隨著醫學與遺傳學的蓬勃發展,大約在1890年代之後,「優生學」也成為西方國家人口健康政策的主軸。許多樂觀的生物醫學研究者認為,牲畜與農作物可透過品種改良來提高產量,「優生學」也可以協助人類培育更健康、更聰明的下一代,並減少身心理有缺陷的族群。此時盛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論者也主張,應該讓不適合生存的族群自然淘汰,甚至應主動除去罪犯、病患,以維持優質的人口品質,也減少社會負擔。
西方國家致力於衛生改革與傳染病管制,使得人口死亡率明顯下降。到了20世紀初,傷寒、霍亂、鼠疫和白喉等傳染病,已不再威脅西方社會。傳染病得到控制,取而代之的是心腦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等退化性疾病,以及現代化社會越來越普遍的心理疾病問題。
隨著疾病型態的轉變,「健康」的定義也隨之變動,當代社會,人們除了避免死亡、預防疾病、延長壽命之外,也更加著重身心靈及整體生活品質的提昇,「健康」的內涵更為寬廣。然而,對於貧窮國家與人民,基本生存權仍是重要議題。全球化之下,健康不平等問題日益惡化,並未隨著醫學與科技知識的進展而消弭。
四、 公共衛生的早期發展與專業化過程
至20世紀初期,隨著人口健康問題的擴大,公衛專業人力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不管是基於富國強兵的政治經濟考量,還是基於保護社會弱勢的人道關懷,此時推動公衛運動的人們有一個共通的訴求,那就是科學。許多人認為,公衛工作需要的是專業的科學知識與精準明確的計算,不能只有政治操作或社會慈善團體的熱情而已,除此,政府機構也需要有大量熟悉公衛專業事務的人員。
因應上述需求,美國聯邦政府於1912年成立了「公共衛生服務部」,大幅擴充政府公衛部門的權責;緊接著美國第一個公衛學院John Hopkins School of Hygiene and Public Health在「洛克斐勒基金會」的經費支助下於1916年成立;1920年代各個大學紛紛成立公衛學院與相關系所,包括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等,公衛正式步入專業化階段。1933年至1939年間,美國羅斯福總統為了因應全球性的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而推行新政(New Deal),聯邦政府的權責因而大幅擴充,公共服務工作增加,其中包括傳染病防治、疾病調查、人口統計、環境衛生改革、工廠安全衛生標準的制訂、食品藥物管理等等公衛事務;在此時期,由於政府經費的大量補助,公衛學院也蓬勃發展(Fee 2003)。
五、參考文獻:
ADDIN EN.REFLIST Beaglehole, R. and R. Bonita (1997). Public health at the crossroa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ee, E. (1997).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h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Oxford Textbook of Public Health - Volume 1 The Scope of Public Health. e. a. Tetels 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5-54.
Fee, E. (2003). The education of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 in the 20th century. Who will keep the public healthy? Educating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22-261.
Hamlin, C. (2002).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health in developed countries. Oxford Textbook of Public Heal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cKeown, T. (1988). The Origins of Human Disease.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Porter, D. (1999). Health, civilization and the state: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Routledge.
Rosen, G. (1993 (1958)).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Tesh, S. (1988). Nineteenth-century debates. Hidden arguments - political ideology and disease prevention policy.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7-32.